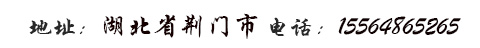郎纪山当年拉煤那些事
|
当年拉煤那些事 郎纪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炕烟需要煤,农户烧锅燎灶,烤火取暖也需要煤。炕烟、烧锅的煤,燃烧时冒浓烟,俗称“烟煤”,多产自平顶山;烤火取暖的煤,燃烧时烟气少,俗称“明煤”,多产自禹县(今禹州),尤以梁洼、白坡、梨园、石蒜臼煤矿的煤最佳。那时,县里设有煤建公司,主要供应厂矿企业、机关及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用煤。因为是计划经济,煤和其他商品一样,不但凭票供应,量也非常有限。生产队及农户用煤得靠自己想办法去百多里外的平顶山甚至更远的禹县拉运。拉运主要靠大牲畜拉的马车和人拉的架子车。个别生产搞得好的生产队“拴”有“一套三”(体壮个儿大的骡子驾辕,两匹马拽捎儿)的胶轮马车,去平顶山拉炕烟煤,起个五更,打个黄昏,百多里地,一切顺畅的话,一天可一个来回。一趟可拉三四千斤,这就节省了不少人力,很使人眼气。但多数生产队穷,“拴”不起马车,拉煤得靠人拉着架子车去运回。当然,去拉煤的都是些青壮劳力。一般一个生产队一趟派出五六辆架子车搭伴前去,为的是路上互相照应。如果一个村有好几个生产队,路上遇着了,一溜几十辆架子车,那场面是很壮观的。出门儿前一天,拉车人又是修理车子又是准备干粮,备齐气筒、锉子、补皮等一应工具。去时,是空车,为了省力,两辆架子车连在一起,你拉我一程,我拉你一程。回来是重载,少则千把斤,多则千余斤,得一步一步“挪”回来。来回三天甚至五天,其艰难辛苦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能体会了的,更是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当年的拉煤人多已作古,尚健在的回忆起当时拉煤路上的情形,吃的苦,做的难,种种遭际,趣闻逸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道不尽。吃加工饭返回的路上,人拉着千余斤的重载,头伸背弓如犁辕,埋头拉车一个劲儿地往前拱,挪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到了饭点儿,见路旁有做加工饭的,停下车子,用“点棍”(盈握粗三尺来长的木棍)支稳车身(免得车胎受重压而散气),拖着快散了架儿的身子向路边的小屋走去。做加工饭的多是夫妻两口,临路搭一间小屋,麦秸苫顶。临门口盘一炉灶,挨着炉灶摆一案板,靠后墙支一张小床,供做饭人晚上休息。做一顿加工饭一人两毛钱,没钱也可用煤抵。因为那时一斤煤就几厘儿钱,钱是很当用的。面是拉车人自带的,做加工饭的只管把面活好擀成面片儿做熟,外加油盐酱醋葱花儿青菜。一天,村上的大娃和二贵从禹县拉煤返回,又饥又累,夜里十点多才遇到一出做加工饭的。二人停放好车子,进了小屋,与做饭人谈好了价钱,称了三斤面粉儿让他们做,并交代:饿了,多添点儿水啊。做加工饭的夫妻二人只顾忙,还未来得及吃晚饭,就故意多添了两瓢水,想着他们要是喝不完的话,顺便喝了,这顿晚饭也就省了。待了一个时辰,满满的一大锅面片儿烧好了,大娃和二贵你一碗我一碗“呼噜”“呼噜”喝的山响,好像没了“对顶”(咽门儿)。做加工饭的在一旁看着,暗想,这一大锅面片儿你就是个牛肚子也喝不完。眼看剩了一个锅底儿,大娃问二贵:你喝了几碗?我喝了七碗。你哩?我喝了八碗。干脆,咱俩松松裤腰绳儿,饶下去吧!结果,大娃喝了九碗,二贵喝了八碗,肚子涨得像个蚰子葫芦,要是打个嗳呒,饭食就会漾出来。做加工饭的妇女边收拾碗筷边嘟囔:没见过您俩恁下喳(土话,下作,吃的快又吃的多),忙活半夜算是给狗剃了个头。两人自知理亏,听见了也装着没听见。住干店夏天拉煤一般不住干店。啥时候该休息了,车子一停,“点棍”一支,铺盖往车下一伸,一个晚上就对乎过去了。冬天不住干店不行。天太冷,出透了汗,住在外边容易伤风感冒。这是人出门儿在外的大忌,所以,有时候该花的钱不能省。所谓干店,一个大空院,一溜儿十多间房子,没有床,大通铺,简简单单的铺盖,也不供应饭食,顶多供应个茶水。这种条件,收费自然是很低的。因为来投宿的都是下力人,条件好了也住不起。如此简陋的住处,对于远道拉煤的人来说,无疑是沙漠旅途中的绿洲,夜行人远处的灯火。负重行走了一天,累的直往地上栽。有了个歇脚处,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可以和天南地北的人东拉西扯,你想得劲不得劲。村上有个叫青凡的,一次和一帮人去禹县拉煤,晚上住了干店。恰巧干店附近演电影,有人撺掇着去看。青凡说:累的跟“憋屁鬼”样还看电影哩!再说了,有啥看头儿,结局还不是咱胜。众人一听,觉得就是那回事儿。那时候演的电影片子,无论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片儿,还是《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等,结剧都是打败了敌人,我方取得胜利。自此,就留了个歇后语:青凡看电影----还是咱胜。后来,越传越远,好几个县的拉煤人都在传,但就是不知道青凡到底是哪里的人。还是村上人拉煤住干店的事儿。村里有个叫二程的人,一年冬里去禹县石蒜臼煤矿拉煤,晚上住到干店里。这天夜里,东北风带哨儿,天冷的不行。快明的时候,二程实在憋不住了,就披衣小解。刚一开门,冻得牙格格响。见四下没人,走到拐角处,想就地解决。还没来得及方便,一披着大衣的老者,大概是干店里巡夜的,用手电筒照住了,大声吆喝:恁大人了,尿哪呀!没厕所!二程反应快,随口答道:咋?咋?不让掏出看看!老者走近一看,见真的没有方便,笑着说:弯儿转的可怪陡!拉坡拉煤的路上坡多平路少,尤其是禹县境内。像芦芬桥的缓坡一般不需要人帮忙,自己独“扛”。遇着稍陡一些的坡,得两人或三人一辆一辆往上“盘”,下坡的时候,一人扛住车杆,车尾耢着地,一人或两人踩住车尾,身体使劲儿往后仰。若遇着假期或星期天,就有半大小子牵着牲口站在路旁等着拽坡,但不是白拽,根据坡的长短,三毛五毛不等。经常出门儿的拉煤人,不怕出力,就怕花钱,能省一分是一分,一般不雇牲口拉坡,只是不常出门儿或身小力薄的拉煤人,图省力才舍得花钱雇牲口拉坡。拉煤人常说,上坡不用怕,有上就有下。意思是说,上坡虽说费劲,但下坡轻松,还是出恁些力。当然,这是就慢坡而言,陡坡就不是那回事了。村上有叫大克的,一次去禹县白坡拉煤,回来时遇一不是很陡的坡,想着自己一人能够溜下来。不料想,车重,把不住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冲。大克吓的腔儿都变了:救人啊!救人啊----周围无人,再喊人也听不到。也算他命大,坡路上恰有一块突出的石块,车轱轮碾上去,下冲的车子变了方向,车干杵到路边一墙上,把墙戳了个大窟窿。。。。。。同去的人等了好半天不见大克下来,折返回去一看,个个唏嘘不已:差乎坏事,错脚错手非出人命不可。接车拉煤人的力量头儿不一样,脚力也不一样,架子车底盘新旧不同,路上作难是常有的事儿。村上有个叫丙兰的人,身柴体轻,第一次出门儿拉煤,路程还不到一半就累“趴”了。可路上谁也顾不了谁,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想起自己路上做的难,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算是自我安慰吧,走着走着竟诌出几句顺口溜:我丙兰今年二十三,拉煤去了平顶山。我体重九十斤,拉煤九百斤。走一步,跟一步,一步不走就站住。我说住(住干店),您不住,都不知我顶住顶不住。不怨天,不怨地,只怪我丙兰没力气。人家力大吃白馍,啃个黑窝窝也不亏我。罢、罢、罢,不再说,不再提,人家烤火不眼气。冷天就是冻死我,再拉煤算我丙兰没囊气。当然,这多少有点儿演绎。但,说拉一趟煤脱一层皮,一点儿都不虚夸。村上还有一个叫泰安的,四十多岁,有力气,就是平板脚,俗称“鸭娃儿脚”。这种脚,脚力差,不能连续走远路。跟人一路儿去拉煤,一停下来休息,“喇叭头”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咋歇都中,别人一说开腿走,就不乐意。本来眼就大,谁说走,就拿眼狠“剜”:急啥哩,能到不家!有一次,生产队派泰安一帮人去平顶山拉炕烟煤。返回时没走多远,一个叫群亭的着凉感冒,四肢乏力,车子拉不成了,没办法只好给家发电报派人来接。为了省钱,电报不用标点,文字尽量简略。本来是群亭病,接。但又怕队上误会逃懒,在后边署上了泰安的名字。因为泰安年龄大,办事也比较稳妥。这样一来,内容就变成了:群亭病接泰安。队上接住电报一看,群亭病了,泰安是“鸭娃儿脚”也得接。于是就派了两个壮劳力连夜去接。赶到一看,泰安好好的不需要接,闹了个误会。既然有人接,泰安就趁腿搓麻绳儿,也说累“趴”了,车子交给了接车的,自己拽了个偏捎儿。拉煤人一到家,煤一卸,心劲儿就落了,半步就不想走。挨到家里,门限儿迈着都困难。第二天,眼肿的合缝儿,腿肿的像个辘轳轴。唉,人就是不一惯,要是还在路上走着,啥事儿也没有。人,其实就是一口气!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拉煤已经成了一个缥缈的传说。作者简介: 郎纪山:男,年生,教师,舞阳姜店郎庄村人。漯河市作协会员。作品多 编:马永红副主编:梁涌泉 李景超 王海方 董晋生 编 委:陈洪涛 赵根蒂 周金生包素娜 魏军涛 史二阳 马永明蔡军英 薛文君赵泮杰余红丽 当班编辑:史二阳魏军涛 审校编辑:马永明 投稿须知: 1.来稿需反复检查,杜绝错别字,并文责自负。 2.本刊对所录用稿件有删改权。来稿请附作者简介、生活照一张、通讯地址、联络方式、最后注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suana.com/sszc/9919.html
- 上一篇文章: 第二节长在心坎上的风物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