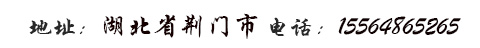开到田里的龙爪花
|
四十年前,在我老太还活着的时候,她家屋后有一条靠河边的田埂,少人行走。一条路没人行走,杂草就会自动生出来,时间一长,杂草有小孩心口高。这条南北向的田埂小孩子一走进去,大人是找不到的,要寻的话,只能屋前屋后放声地喊:丫头,丫头,家来吃饭了!这样的声音在乡村饭点时,不时地出现,此起彼伏,远远地传出去,又从遥远的地方呼应过来,搅和着炊烟。 不在饭点的时间,小人儿就趴在这田埂上。某日正在寻蚂蚱,突然发现昨日压倒的草旁长出了一枝花,长长的枝干伸出在草尖上,就像一个农人,在麦田里正劳动时忽然直起了腰,看一看头顶的太阳落到哪里去了? 这朵头发蓬乱,没有叶子的怪花,正在努力地向上拔节。小孩伸出小手掐下它,把花序上排列的一朵朵小花摘下来,和平时一样尝花茎里有没有一丝甜味。把东西放嘴里品尝是一种天性,是饥饿舌头的本能,小孩子是不知道有个尝百草的神农氏的,在春天拔出茅草丛里的茅针当零食吃是舌头对手发出的邀请。这朵红花转眼间,就被肢解掉,火红的花瓣和花蕾乱糟糟地落在草叶上,所有肢解过的花茎都被吮吸过,柔嫩的枝干变成褐色的残渣。 那时候我还不懂花的含义和它们的使命。我捕捉白蝴蝶是因为它们自由,它们会脱离大地的羁绊,转眼间就去了我不知道的远方;我也摧残这些美丽的杂草,它们从泥土里出生,注定了要被人果腹。 我见过花这样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妈。她的眼中只有头顶的蓝天和脚下的庄稼,她的锄头下只留得下玉米苗、黄豆苗和山芋苗,还有小胡萝卜缨子,别的都是必须锄去的草,哪怕这些花只长在不起眼的田埂上。我爸也不明白花是怎么回事,他除了工作,就是想怎么样省钱,怎么样才能把月头拿到的工资省到月底还有得用! 除了小孩子知道有美丽的蝴蝶和花,除了小孩子会幻想有一个童话的世界,里面长满了能吃的花花草草,大人们谁又在意呢?所以那样野生的一枝独花,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花,又是怎么来的? 再见到那花,让我激动了半天。在老丰中小花池边上长了一排卷曲的、耀眼的红花,很像一队头插羽冠的士兵,整齐的一溜儿排出去,光溜溜的枝干,不见一片叶子,花硕大而无香。 我惊讶人们用砖砌墙,把土地围成一块块长方形的、椭圆形的小花池,甚至在拥挤的大马路上也有这样的花池,栽上不能做椽子的矮桩树,和这些美丽的花花草草挨挨挤挤,美其名“绿化”。就在进城前,我栽在屋前田边的几株菊花,连花苞都没来得及打,就被我妈当杂草锄去了。 之后,城里的绿植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高。当人们站到高楼的窗口向下看草坪和草坪里栽的高低起伏的景观树的时候,他们开始怀念乡村,怀念小时候拔过的茅针了。 认识潘园是今年最愉快的一件事。竟有人真的造了一座院子以长花草为生,日日与花为伴!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惊艳之举!我一边惊叹,一边频繁地来来去去。我们人类有时也会有动物性的行为,就像一个饥饿的小蚂蚁发现了一堆美味的饼干屑,一个个触须相连,心意相通的朋友来了。大家把潘园当作自家的后花园,游玩、拍照、摘果子、插花、打牌,甚至我还在荷花池的小码头摸过田螺。长满绿苔的田螺懒洋洋的,又大又肥,一把把从淤泥上摸出扔到水泥石板上,堆了一小堆,然后摘一片大荷叶欢喜地包好带回家。 潘园大规模的花事是绣球花开的时候,几个大棚、所有的花径、河边,摆满了十几个品种千姿百态的绣球花,引得看花的人比穿梭的蝴蝶都多!园主潘春屏说,绣球花我是世界第三,石蒜花我却是世界第二。 潘春屏是个好玩的人,他花白的小胡子翘在下巴上,每每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这样一个书生意气的人却是国内外有名的园艺师,在央视做过访谈,头上有无数中国之最的头衔。 石蒜花就是园主说的彼岸花,我们称为龙爪花的那种。彼岸花!那个有着许多传说的花,让人充满期待。在绣球花花开正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雀跃,想象潘园的彼岸花和小时候偶遇到的花有什么不同! 一个月后,潘园不断地传出信息:在栽石蒜;在移植石蒜。我把发芽的山芋秧栽到潘园去,在一处偏僻的大棚里发现了许多像山芋秧样的植物,只是叶片金黄和我拿去的紫色叶子不同,一问是真的山芋秧,就以叶片精美著称。 山芋秧也能做观赏盆景? 不是的,是为了衬托石蒜花。园艺师不解说,你永远不知道用途。没有叶片的石蒜花需要人工造叶,点缀花之美。 没几天,石蒜花开了的消息就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suana.com/sszc/9903.html
- 上一篇文章: 四季美景不同,堪比ldquo城市花园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