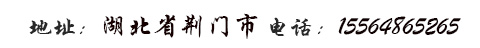孟郊一首游子吟,刷爆年前朋友
|
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唐代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现存诗歌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因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据《旧唐书》及线装本《唐诗三百首新注》记载,说他两试进士不第,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其欣喜之情,可於《登科后》的二语中见之。越四年,任溧阳县尉。由于不能舒展他的抱负,遂放迹林泉间,徘徊赋诗。以至公务多废,县令乃以假尉代之。后因河南尹郑余庆之荐,任职河南,晚年生活,多在洛阳度过。宪宗元和九年,郑余庆再度招他往兴元府任参军,乃偕妻往赴,行至阌乡县,暴疾而卒。孟郊仕历简单,清寒终身,为人耿介倔强,死后曾由郑余庆买棺殓葬。故诗也多写世态炎凉,民间苦难。 深情不及久伴, 这世上最好的孝顺, 莫过于常伴身旁。 父母子女一场,不是看着对方的背影渐行渐远渐无书,等到蓦然回首,那人早已不在灯火阑珊处;而是我们互相参与对方的生活,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年,香港评选最受欢迎的十首唐诗,排在首位的是《游子吟》。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而那年写下这首诗时,孟郊已经五十岁了。诗人早年漂泊无依,穷愁终身,直到天命之年才得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官职,结束了长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仕途失意,饱尝世态炎凉,眼看高堂明镜悲白发,愈发觉得亲情之可贵,于是发自肺腑地写出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颂母之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大部分人牙牙学语时便含在嘴里的诗句,然后蔓延一生,最终化为心底一份挥之不去的乡愁。 唐天宝十年(年),孟郊出生于湖州武康,父亲孟庭玢是一名小吏,在昆山做县尉,家中清贫。孟郊从小生性孤僻,很少与人往来。 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喜欢搬弄诗句,常在饭桌上与父亲对联,若是对得好,父亲就会赏他一杯酒。 长此以往,他的对联水平突飞猛进,小小年纪便因对联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且因此养成了饮酒赋诗的嗜好。 某年冬天,有个钦差大臣来到武康县体察民情。县太爷大摆宴席,为钦差大人接风。孟郊仗着熟悉地形,悄悄混了进去。 县太爷看到破衣烂衫的孟郊,眼珠一瞪喝道:“去去去,小叫花子,一边去。”孟郊很不服气地顶了一句:“人有长幼,不分贵贱,离地三尺有神仙。” 钦差大臣觉得孟郊挺有意思,于是自恃才高地要出对联考他。接着钦差大人摇头晃脑地出了上联:“小小青蛙穿绿衣”。 孟郊当时正穿着粗布绿衣,知道这是在奚落他,见这位钦差大臣身穿大红蟒袍,又见席上有一盘煮螃蟹,略一沉思,对道:“大大螃蟹着红袍”。 钦差一听,气得浑身发抖,但有言在先,又不好发作,便对县官说:“给这小儿一个偏席,赏他口饭,我再和他对对。” 这老钦差三杯浊酒下肚,又嘚瑟开来,他斜了一眼孟郊,拉长声调说:“小小猫儿寻食吃”。孟郊看着恶狗扑食般的钦差大臣,又看了看溜须拍马的县太爷,怒气冲冲地回敬道:“大大老鼠偷皇粮”。 钦差大臣此行正是为“皇粮”而来,听罢吓得目瞪口呆,出了一身冷汗。最终,此次酒席交锋使得孟郊名扬全县。 好景不长,孟郊10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裴氏含辛茹苦地将他与两个弟弟孟酆、孟郢抚养成人。 年轻时的孟郊极有抱负,挥洒自如,运斤成风:“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我愿分众巢,枭鸾相远居。此志谅难保,此情竟何如?” 孟郊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对外面的世界抱有极高的期望,认定“物皆备于我也”。 然而,命运并未因此眷顾于他。大唐王朝,虽是盛世,寒门学子的出头之路却也有限。 孟郊即便有满腹才华傍身,参加科举,仍然屡试不第。据现代学者范新阳的研究,孟郊曾“十七年间六落第”。在母亲的殷殷期盼下,孟郊并未放弃,直到41岁才中了吴兴乡贡。兴冲冲来到长安应考,满以为能从此一朝得道,鸡犬升天。 谁知现实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次考试,孟郊落第了。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落第》一诗。 落第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 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 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 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 孟郊以雕鹗自诩,却不料科举落第;而那些“鹪鹩”般胸无点墨的无能之辈,通过投机取巧却能官运亨通。 所以孟郊觉得天地失色,日月无光,连姹紫嫣红的无边春色都蒙上了严霜,落第后的那种失落感,再好的风光都让人怅惘。 当他第二次来到长安时,结果依然是铩羽而归。悲愤抑郁的他挥笔写下《再下第》,一个“再”字饱含了无尽心酸。 再下第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 再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这次落第之后,孟郊彻夜无眠,想起这一路的颠簸劳碌,不禁涕泗横流。“空将泪见花”,是以乐景写哀的典范。 王夫之曾经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首五言绝句虽然短小,所表达的痛苦却颇为深长。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在受尽了命运的捉弄之后,公元年,两考两败的孟郊奉母命第三次赴京科考,终于得登进士第。 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胜,挥毫写下生平第一首快诗《登科后》。 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科举时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虽然已经46岁,孟郊此时中举却也不算太晚。困顿已久,一朝中举,可谓是出尽风头。 京城的鲜花美景看遍,如花美眷赏过,可是烈火烹油之后苦难并未如烟尘般散去。按照规矩,考进士由礼部主事,中榜后并不授官,只是具备做官的资格而已。 踌躇满志地看尽了“长安花”,孟郊在家徒四壁的凄清中苦苦等待,直到公元年才等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官职。 也是在这一年,孟郊在迎接母亲到身边奉养之时写下了那首感人至深的《游子吟》。 孟郊以文人任武职,避长用短,做官并不称职。在任期间,孟郊常常疏于政务,放迹林泉间,徘徊赋诗,耽于享乐。 这样的行为自然招致县令的不满,于是报告上级,找自己的亲信来代他的职位,并罚半俸。韩愈因此称他为“酸寒溧尉”。如此一来,他本就清贫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这大概也是他“苦吟”的缘由之一。 生活如此窘迫,这个被元好问称为“诗囚”的孟郊却并未因此改变自己,依旧一心投在作诗中。他作诗非常谨慎认真,往往苦思力锤,雕刻其险,颇有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孟郊的妻子在长年的凄苦生活中积劳成疾,驾鹤西归。不久之后,孟郊罢任溧阳尉,闲居洛阳。 公元年,郑馀庆上奏请孟郊为水陆运从事,出任试协律郎。能有此官职,还得归功于做溧阳尉时,韩愈写的一首《荐士》诗。同年,孟郊续娶郑氏,在洛阳定居。 两年之后,孟郊于58岁时连丧三子,伤心悲恸无以言表。暮年失子,一贫如洗,使得孟郊只能将一腔愁苦付诸笔端,写下数首苦吟诗。 60岁时,孟郊因为母亲去世而丁忧居丧。五年后,郑馀庆转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又奏请孟郊为参谋。孟郊带着妻子前往,却不幸在阌乡暴病而亡。 史载,孟郊死时,“家徒壁立,得亲友助,始得归葬洛阳”。韩愈为其作墓志铭,张籍倡议私谥曰贞曜先生,故韩愈题《贞曜先生墓志》。 幼年失怙百事谙,晚岁穷愁形影单。留得清寒苦吟句,游子天涯竟何堪?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惨事都被孟郊一人碰上了。 用倒霉催一词来形容其一生,一点儿也不过分,好事从来不会眷顾于他,背运一直相伴左右。 不善于官场逢迎,大唐盛世又如何?“诗人”这顶桂冠再怎么荣耀无限,却也难以兑现一个现世安稳。 于孟郊而言,他一生都囚在了诗中,从未走出! 在《祭十二郎文》中,韩愈一再提到孟郊:“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韩愈与孟郊,同为“韩、孟诗派”的创始人,诗歌主张和风格比较接近,而且交往较多,情谊深厚。孟郊比韩愈大17岁,彼此相交22年,自始至终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年,韩愈与孟郊同考进士,韩愈榜上有名,孟郊却名落孙山。孟郊落榜后心情压抑愤懑,作《长安道》以宣泄。诗曰:胡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韩愈来看望他,并写诗安慰《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韩愈虽然自己登第,但他深切理解穷书生在落第后的复杂心情,因而他安慰和勉励孟郊是情真意切的。他们的结交,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了。孟郊离长安东归,韩愈又写《孟生诗》举荐他入徐州张建封幕。孟郊接受了韩愈的建议,在准备前往徐州之前,作了一首和诗《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以回应韩愈。诗中用了孟郊式瘦硬的风格来写离愁:“富别愁在颜,贫别愁销骨”“离弦不堪听,一听四五绝”;写自己的现状:“懒磨旧铜镜,畏见新白发。古树春无花,子规啼有血。”两人始于精神契合和相互扶助的友情已然起程,其后两人又有过八次重逢,其中有四次留有唱和作品,由此更加深了友情。年,孟郊中进士,并与韩愈聚首。期间两人作诗应和,相得无间。孟郊年,韩愈为孟郊作诗“……,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愈生平自负,轻易不赞许别人,但对孟郊十分敬重。他把自己和孟郊的关系,以李白与杜甫相比,说明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更表明他渴望与孟郊在诗坛称雄的志向。 同年,汴州暴乱。韩愈逃亡徐州。处境困窘之时,更加怀念知心老友孟郊,为此作《与孟东野书》,抒发内心苦闷: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脱汴州之乱,幸不死,无所于归,遂来于此。主人与吾有故,哀其穷,居吾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因被留以职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复辞去,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来相视也。自彼至此虽远,要皆舟行可至,速图之,吾之望也。春且尽,时气向热,惟侍奉吉庆。愈眼疾比剧,甚无聊,不复一一。愈再拜。 年,孟郊当上一个小官,并把老母接到身边奉养。但是他以文人任武职,避长用短,不易称职,被降半薪,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三年后,孟郊才遇韩愈,苦闷得以诉说。韩愈以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写了《送孟东野序》,鼓励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成就。《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年,孟郊辞职。韩愈被贬。元和元年()两人再次相逢于京师,创作了11首唱和诗,且均为联句,由此将两人的感情、诗思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联句中,两人互道遭际,倾诉相思之情: 剑心知未死,诗思犹独耸。孟郊 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韩愈(《会合联句》) 微然草根响,先被诗情觉。…… 危檐不敢凭,朽机惧倾擈。 青云路难近,黄鹤足仍鋜。孟郊 与子昔暌离,嗟余苦屯剥。 直道败邪径,拙谋巧伤诼。…… 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韩愈(《纳凉联句》) 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孟郊 月光有时晦,我心安所忘。韩愈 常恐金石契,断为相思肠。孟郊…… 苟无夫子听,谁使知音扬。韩愈(《遣兴联句》) 自从别君来,远出遭巧谮。韩愈…… 欲知心同乐,双茧抽作纴。孟郊(《同宿联句》) 一则以情,一则以志,韩愈和孟郊在唱和诗中不断重复着这两个主题,他们的友情也在知己之音的回应下变得牢不可破。南宋人王十朋读韩孟联句亦有如是体会:“韩退之之留孟东野也,其诗有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某初疑退之言为夸,及观《城南》诸联句,豪健险怪,其笔力略相当。……然后知‘复蹑’之语为非过。又读其末章有曰‘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于是又知二公心相知、气味相得,至欲相与为云龙而不忍有离别,真可谓古之善交者。” 年,孟郊58岁连丧3子,凄苦悲恸无以言表。韩愈写《孟东野失子》,对老友进行劝慰。元和九年()韩孟阔别多年,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唱和,孟郊在洛阳先赠韩愈诗云:“何以定交契,赠君高山石。何以保贞坚,赠君青松色。”表达两人友情的坚固;又向韩愈提出建议:“众人尚肥华,志士多饥赢。愿君保此节,天意当察微。”(《赠韩郎中愈》)。韩愈对朋友的情之厚、劝之衷做出回应:“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江汉一首答孟郊》)始终以古道忠义相吸引。同年,孟郊去世,葬于洛阳北邙山。韩愈作墓志铭。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九年,随着22年时光的流逝,两人的友情在一次又一次的唱和过程中不断重温和巩固,最终成了挚友,他们以坚固的友情和高尚情操挑起了中唐诗派的一杆大旗,走出了一条新的诗风之路。纵观韩孟交往史,虽偶有得意之时的应和,但更多的是失意时的劝勉,困惑时的帮协,窘迫时的慰籍,以及处在人生最低谷时的陪伴与扶持。可见,朋友间锦上添花尚且容易,雪中送炭则尤可珍贵。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朋友更替的频率也随之加快。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朋友,过了这个时期,朋友就疏远了;一处地方有一处地方的朋友,离开这个地方,朋友就不联系了。手机“朋友圈”里几十甚至上百号的朋友,充其量只算是熟人,称得上真正朋友的,有一个就不错了吧。现代人已经习惯了互相包裹着真心,彼此提防着,这种叫有爱无心,在热热闹闹的朋友圈里,冷冷清清地过着没有朋友的日子,回望古人,倍感惭愧,倍感羡慕。 《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年代:唐作者:孟郊 富别愁在颜,贫别愁销骨。懒磨旧铜镜,畏见新白发。古树春无花,子规啼有血。离弦不堪听,一听四五绝。世途非一险,俗虑有千结。有客步大方,驱车独迷辙。故人韩与李,逸翰双皎洁。哀我摧折归,赠词纵横设。徐方国东枢,元戎天下杰。祢生投刺游,王粲吟诗谒。高情无遗照,朗抱开晓月。有土不埋冤,有仇皆为雪。愿为直草木,永向君地列。愿为古琴瑟,永向君听发。欲识丈夫心,曾将孤剑说。 《送韩愈从军》年代:唐作者:孟郊 志士感恩起,变衣非变性。亲宾改旧观,僮仆生新敬。坐作群书吟,行为孤剑咏。始知出处心,不失平生正。凄凄天地秋,凛凛军马令。驿尘时一飞,物色极四静。王师既不战,庙略在无竞。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气定。今朝旌鼓前,笑别丈夫盛。 ------------------------------------------------------------- 注解1:“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贾岛。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注解2:韩愈和孟郊都是中唐时代的重要作家,两人的名字常常被相提并论。韩愈的同时代人赵磷在其《因话录》卷三中说道:“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可知中唐时已将韩孟并称,并说两人颇有交情。《旧唐书》记载:“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可见韩愈和孟郊的深契交情,是由韩愈首先倾心拜服孟郊开始的,他们的友谊形成了真正的“忘形之契”。宋、明和清代都有诗论家认为韩愈以其才气、名声和权势自成一派,张籍、李贺、刘叉、贾岛等诗人皆可谓游于韩门者,但韩愈对于“韩门诸人”,“所心折者,惟孟东野一人”。今人更以韩孟来指代中唐的这一支诗歌创作群体——“韩孟诗派”。 yue时光荏苒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suana.com/sszc/10097.html
- 上一篇文章: 图说地理中国赏秋地图
- 下一篇文章: 寺庙中的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