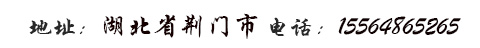风雨兰开了
|
北京治扁平疣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629850.html 痕迹 01 风雨兰,不是兰花。 百度上资料上写,「石蒜科葱莲属多年生草本」。六月以前,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 直到某天,一位豆瓣友邻发了几张图片,写道“风雨兰开了”。 看到图片里开得正好的粉色花朵,我突然想起了外公。小时候,外公在自家院子边的两只废铁桶里种了两簇这样的小花。 那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后来工作有些忙,加上自己的惫懒,又搁置了。 风雨兰开了——我的外公(1) 外公的身体不好,自我记事起,就被风湿病所困扰,他总是静静的编蔑筐、收拾柴火、给我做饭,唯一的爱好似乎是逛庙会吃两元钱的自助斋饭。 外婆的家里,也没有什么摆设,屋里没有,院子里更没有。那两个破烂的铁桶里的花,像是最后一点外公的闲情逸致。 外公,和那个院子,都在十年前没了。 我现在常常不能想起他,突然有些害怕,就这样把他忘了,但那花的味道还在脑子里,于是想尽力从脑子里拓出些不完整的记忆。 ↑ 你看,上面我脱口而出“外婆的家里”,前一句明明还在讲我的外公。 外公就是这样,仿佛是家里的边缘人物,尽管在两个女儿出嫁之后,这个家里就只剩下了他和外婆两个人。他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关系,习惯活在外婆的“荫蔽”之下。 他的话很少,甚至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我们浩浩荡荡一行人回老家看他和外婆时,他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有任何的不适,大家的焦点在外婆身上,她在一个月前刚摔伤了手。 我不知道外公和外婆之间这样的“强弱”关系,是两人初遇时就如此,还是结婚之后开始的,又或者,是从他的风湿病发、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开始。 他的个子不高,甚至有些矮小,在受到风湿病折磨的几十年后,身体愈发蜷曲,但脸上似乎总是笑盈盈的。外公的笑是内向的,腼腆的,像是小心翼翼的取悦,有些温吞,是安静的,不像有的中年人,笑声浮夸,带着太多的社交目的。 外公去世的那天 我的外公叫李运文,40年代生人,死于年2月7日,农历正月十六。那一天,是我大嬢的生日。 我正在大嬢家的院子里吃饭,我记得那天人来得很齐,好久不见的堂姐带着她新婚的老公,第一次和这么多的亲戚见面,围坐了两桌。饭点的时候,我的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周围的人神色开始有些怪异。 我大伯的妻子是个长期生活在城里的,医院有工作的女人,她最先提到了这件事,问我:“雨儿,你知道吗?” 我记不得后面发生了什么,只记得父亲当时的妻子开车送我们到外婆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年初二时我们才和大姨一家一起去探了外婆的病,当时完全没有人察觉出外公的异常,这一定是一场玩笑。 在距离外婆家几百米外的柏油路上下车时,外公已经被装进了殡仪馆开来的车里。大姨和她的老公已经在车上,我和爸爸也坐了进去,外婆不在,她按规矩不能参加这个过程,不能送自己的老公最后一程,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忌讳。 外婆弟弟的儿子,建平表叔,作为关系较近的晚辈,也和我们一起上了车。 殡仪馆的车从罗江南塔的加油站拐弯,向回龙方向开。外公火化的地点,和妈妈火化的地点在一处。火葬场的人员把外公从专用的密封箱里推出来,在同一间火化炉的面前,我第二次见到亲人的遗容。 外公的脸上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笑容,平静中稍有一点悲伤,面色有些暗下来,但眼睛闭得紧紧的。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人在这时候是否总是有些恍惚,在之前的漫长过程里,我都没有流泪。记得大家都像是在完成某种任务,推进着这件事。 直到火化过程中,在那时候的我眼中漫长的等待里,建平表叔对我说了一些话,才终于遏制不住得开始掉眼泪。后来的十年里,直到现在,我想起外公,仍旧会忍不住掉眼泪。 建平表叔说的话很简单,无非就是外公总是放不下我,对我有期待,希望我更好,要对得起他的付出和期待。 而我回忆起外公,总是他在自己的院子里,在所有人视角的边缘,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温柔、退让。他的一生太苦。 大二的一门课上,老师让我们写家史,我在询问大姨和外婆之后,对他的一生稍多了些了解,现在那份作业早就不知所踪了。我应该重新为他写点什么。 8月19日下午,又在网络上看到了风雨兰的照片,这次是一位在B站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suana.com/sszc/9743.html
- 上一篇文章: 警惕叶片发黄发软发蔫有可能是烂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