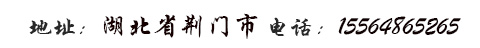怀念母亲
|
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在那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提示:点上方"幸福监利"↑↑↑免费订阅 --传递正能量,汇聚监利思想者 --投稿请联系/ 怀念母亲 文:甘肃/彭明勋 我的家乡在陕南大巴山区,母亲生在解放前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没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但她会背“三字经”和“百家姓”。对这种传统文化的启蒙和印象最早是母亲给我的。母亲缠过足,走路不是很快,但她年轻时身体很好,她的能干,在乡里是出了名的。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8个子女。父亲自50年代就是大队干部,一干就是30年,他常年在外忙,从不管家务。早年他们弟兄5人分家时,年迈的祖母执意要跟贤惠的母亲过。我们家孩子多、拖累大,但母亲毫无怨言,直到60年代才把祖母送老归终。在生活极其困难的年代,母亲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大的要谈婚论嫁,小的正嗷嗷待哺,其难度可想而知的,两位长兄结婚后,全家共10多口人,母亲又是上有婆,下有媳的多重身份,整天面对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还要平衡婆媳、妯娌、姑嫂等各种矛盾关系。是母亲用她的坚强和双手,撑起了一个自始至终都没分家的大家庭,这在乡里人看来是极不容易的。更让人对母亲佩服的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我们这些子女都没学坏,尤其让她们欣慰的是:大哥、二哥很早就成了乡里少有的国家干部。其实,由于当时家庭太困难,两位长兄读书也不多,刚上中学就辍学了。大哥离校时,老师、学生和家长都痛哭流涕,后来几个姐姐也失去上学的机会。母亲每谈及这些和长兄勤奋刻苦的学习往事,总是内疚地自责。贫困的家庭永远为子女所累,母亲的苦难多半都是因我们这些子女造成的,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母亲是凭怎样的毅力和强烈的母爱,让自己的孩子渡过了艰苦的岁月、养育成人的哟!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因为家里子女多、劳动力少,每年分红,我们家都要超支。母亲每天不但要没日没夜地劳作,最艰难的莫过于全家吃饭问题了,那点能照着人影的稀饭还不够孩子吃的,母亲自己只能用野菜、野果、糠皮充饥。有一年,山上的野菜没有了,地里的红薯根已经翻过几遍了,所有人都开始找“代食品”。母亲听人说老鸹蒜(石蒜,有毒)和芭蕉根好吃,便从山上挖来捣碎加点玉米粉烙成饼,又采来“竹米”(竹子开花后结的籽)做成稀粥。这在当时没有断粮已算很不错了,但那味道实在无法下咽,还笑话母亲:听人说什么好吃,就当真了!而母亲却一人在那里默默的大口吃着。那知,当时家里已无米下锅了。我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打我记事起,母亲就特别疼爱我,老怕我受冻挨饿,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还给我煮“罐儿饭”开小灶,即便实在没办法,也要从稀的里面捞稠的。尽管享受这种特殊待遇让我很不自在,但母亲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在我的记忆中,自上小学开始,母亲不分春夏秋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做早饭。出门时她总要站在门前的那棵树杈上,一直目送我翻过房前那座山梁,年年如此,岁岁这样,直到初中住校,每星期回一次家,母亲又把我当客人一样,总要做家里最好吃的饭菜。母亲自己的衣裳不多,甚至都打了补丁,但出门时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母亲的围裙是和上衣连为一体的,几乎常年不离身。我们家跟其他子女多的家庭一样,衣服多是接上面兄弟姐妹的穿,尽管是旧的,破烂的,经母亲的手一拾掇,也不比别人家的孩子穿戴差。母亲过怕了缺吃少穿的日子,每年都要种很多蔬菜,养不少家畜家禽,年年都要喂一到两头“过年猪”,这在过去的家乡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年到头连猪都“杀”不起,那就是主妇的失职,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勤劳兴旺的标志。每当过年过节时,母亲是最繁忙的,为了让子女吃好穿好,她会几天几夜不睡觉。现在想来,母亲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把她对子女的那份爱连缀在了一针一线上!母亲一生都无愧于一个善良女性的称谓。尽管她一生手头上都不宽松,但她从没间断对比我们更拮据的人的接济。在我们自己都靠吃救济粮度日的年月里,她义无反顾地接收了七、八岁便失去双亲的表兄表弟,这样一住就是几年,别人不理解,自家人也有怨言,但她硬是顶着压力,从自己的饭碗里“抠”出来一些,干的按照稀的做,吃穿当自己亲生的对待,最终将两位无依无靠的孤儿拉扯成人。对家庭极度困难甚至讨口要饭的人,母亲也从不呵诉、从不歧视,总是抱着一颗怜悯之心。 母亲由于操劳过度,不到50岁白发就爬满了头顶。按说,子女大了,本应歇口气了,但事与愿为。年,我中学一毕业就自作主张参加了征兵体检,母亲知道后,伤心地哭了几天几夜。是呀,这是我给母亲的一个很大打击。大哥、二哥很早就在外面工作,接着两位嫂子也先后出去了,还未出嫁的姐姐已定好了婚期。眼看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就指望我来支撑这个家,这时却突然要离开她们!同时,在一辈都处在山乡里的母亲心里,当兵就是生离死别。她常给我们讲:解放前我的一位舅舅去当兵一去不复返,外婆过逝无法闭眼的事,这对她始终是个心结。在新疆当兵的堂兄每次探家临别时,她都要伤心落泪……。更不巧的是,那年正在大队开会的父亲突然得了中风病,半个身子失去了知觉,生活不能自理,这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和全家都无法接受……。这一年真的叫我无法离开这个家。但在第二年,也就是年秋,我仍然打消不了对参军的热情,又一次参加了应征体检,母亲再次以泪洗面,但明显比头一年好了许多。我知道她理解我,可在她内心又是多么矛盾、多么残酷啊!送兵那天,乡上的领导带着鼓乐队来了,亲戚朋友和乡邻都来为我送行,家里锣鼓喧天,鞭炮阵阵,但对母亲来说,丝毫没感到喜庆。她的手是冰凉的,脸上没有血色,只有泪水不断,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掏出不知什么时候用手绢为我一针一线缝制好的,既可以当钱包又可以当针线包的一个饰品,塞到我手里,泣不成声的说:“儿呐……把你栓到家里又苦又累,没什么前途,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吧……”。此时我已泪如雨下,对母亲说:“就当我出去打两年工吧……很快……”,后来是怎么离开的,我的眼前始终是模糊的。结果,这一出就不是几年,而至今都没兑现给母亲的承诺,直到年秋,我仍在千里之外的部队,接到母亲离世的噩耗。母亲几年前就有了肺心病,医院当院长的大哥治疗吃药控制。在病情最重的时候,我曾带爱人回老家探望,那一次,她昏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他的身边哭唤她,她居然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再没事了。临行时,她仍然费力地攀到房前的高坡处,目送我直到再也见不到她渐渐消失的身影……那却是最后的永别。回想起刚离家那几年,母亲无尽的思念真是无以言表。大哥在母亲已望穿秋水,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希望我春节能回去一趟。但母亲却让小妹代她给我写信:“……不要挂念我们,家里一切都好……”,每当看到这里,我那不争气的眼泪总会情不自禁往外涌,仿佛母亲那一双放大了的小脚,踩着信中那淳朴的话语,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我走来……。此时,唯一能安慰母亲的是,我在部队进步很快,几乎年年有立功喜报寄回老家,这自然让她们引以为豪,同时也是我后来没能履行对母亲承诺的一个原因。自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家里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但零用钱仍不宽裕,然而我们的父母只要勉强能过,从来不向自己的子女张口,他们害怕增加我们的负担,这就是她们的秉性。母亲十分关爱她的儿孙。临去世前一个里拜,他在县城两位长兄家,我偶然一个电话正巧她拿起了话筒,交谈中说自己的病好多了,让我放心,只提出要一张她从未见过面的孙女的照片。接着,母亲在回乡里老家时,又依次去了几个姐姐家。辞世前的头一天,刚好收到我寄给她的我女儿的照片,据说她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样,她似乎是无意间和她的儿孙们都道了别。母亲走的很突然,早上一起床她就把从来不会做生意的父亲催去卖几分钱一斤的棕板,以换取油盐钱。自己则张罗着为正患感冒的小妹作开胃的凉拌萝卜丝,刚端到小妹跟前,坐在床上正说话,突然睡过去就再没有起来……。那天是阴历十月初二,秦岭以南的大巴山区气温骤降,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大朵大朵的雪花,一连持续了七天。母亲说过她喜欢老人过世下雪,连大地山林都为她披孝戴花,那一定是生前积了德的。冥冥中我相信这是真的,是上苍以此慰藉母亲的一份贺礼!母亲一辈子操劳,一辈子没享过福,临终时依然在为生计犯难,依然在为子女操心,这怎能不让我这个没有履行承诺、没能在她身边尽孝的儿子伤心欲绝哟!时光如箭,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3年了。想着含辛茹苦的母亲,我却无法报答她那深逾大海般的母爱,唯一只能写下这点文字,当作对她永远的怀念……。(年首载《文学天地》、11月23日载《西凉晚刊》等)下图为年我为母亲留影 本文作者:甘肃武威/彭明勋 彭开全老师推荐 长按以上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suana.com/ssjb/9814.html
- 上一篇文章: 在冬天,这7种球根花卉很火哦
- 下一篇文章: 深吸一口欧气,来看如何种植洋水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