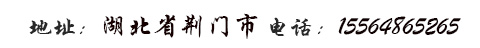尘世走笔彼岸花李晓斌
|
农历七月,秋风渐凉。也许是天高气爽、能见度高的缘故,乡村的夜晚,时常可以看到流星雨从西天划过。村里的老人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又有人老了。 此时节,通往山野的道路边,摇曳着一簇簇红色的花朵。那花,丛生于翠玉簪似的茎干顶端,鹤立鸡群似的探出野草荆棘之上。花蕊一雌六雄,长长的,微微往上翘,比美人的睫毛更令人心动。六片花瓣狭长卷曲,如风情万千的兰花指,在风中传递着舞蹈的韵味。只见花不见叶,宛如从地里冒出的一个古怪精灵。 凄婉的唢呐声嘀哩哩响,龙杆木抬着的灵柩在一队披麻戴孝的送葬人簇拥下,缓慢地行走在两边零星盛开着红色花儿的山道上。这条路,连着祖辈刀耕火种的山林,连着孟婆婆守着的奈何桥,连着先人的坟地。这是一条通往彼岸的路,这一路上闪耀的红艳花儿,就叫彼岸花。 庚子七月初七早晨,我发现阳台上寄生在朱顶红花盆里的彼岸花开了。虽然只有两株,但也给绿意稀薄的阳台平添了一点红。当年,我从寒山的水涧边挖来一只鳞球,转眼它就在我家阳台生长了近十年。时光就像这花儿一样,一年一度花开花谢。 和朱顶红共一个花盆的彼岸花,寂寞无语,很不显眼。朱顶红趾高气扬,犹如贵妇人,占据了花盆所有的空间。彼岸花见缝插针,谦卑恭让,好像一个服侍人的婢女。彼岸花是属于山野的,只有在野外,自由自在的她才能显现出别样的美。不过,彼岸花并没有芙蓉、芍药的肥硕,纤弱单瘦得仿佛经受不起一阵秋风。她不是花中的杨贵妃,她比可以在君王指尖跳舞的赵飞燕更轻盈。她是宋词里的温庭筠、柳永,婉约凄艳,总是让人莫名感伤,甚至泪眼婆娑。 彼岸花是会夏眠的。秋天花谢了,不久就会长出新的长条状叶子,直到翌年的炎炎夏日,叶子枯黄,风雨掠过,彼岸花销声匿迹,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她潜入地下,在土里夏眠,将所有的力量蓄积在球状的鳞茎中,静静地准备农历七月的那场花事。 我是在山野长大的,小时候并不认识这寻常阡陌上的寻常野花。彼岸花最初给我印象的,居然是一帧画片儿,一位画家在一对鸡的旁边勾勒出几笔花。当时,少年的我孤陋寡闻,只觉得墨鸡配红花很好看,并不知道它就是彼岸花。年少的我,痴迷绘画,对于山水花草却多是从纸上认识。我对着那画片儿临摹,只感觉这花儿怪,不仅形状不同于平常花朵,更是有花无叶,和水仙、兰花也不像。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养一头牛,几只猪,一群鸡。早晨上学前,小孩子必须去田野上放牛、扯猪草、钓青蛙。由于先看过了画片上的彼岸花,我在放牛或是扯猪草、钓青蛙时,才注意到,原来,家乡的田头地角,也有这种花,乡民称之为“牛屎花”——也许牛粪给土壤增添了腐殖质,更适宜彼岸花的生长。它的学名叫“石蒜”,生长在石缝里的蒜苗,球茎含有淀粉,虽有小毒,却是饥荒年月灾民充饥的野菜。“石蒜榆皮那得饱,刀耕火种岂能任”,人活到这一地步,真的还不如涉过忘忧川去那无烦无恼的彼岸了。 千百年来,彼岸花就在家乡的陌上开着。它不管红尘事,只知春生、夏枯、秋花。好像我们的先人,一代代在田野上生活着。时光就在彼岸静悄悄地流淌,不闻涛声。 又是一年秋风起。村里的女孩子提着满满的一篮子猪草走回鸡鸣犬吠的小巷,手上总会捧着一束彼岸花。沾着秋露的彼岸花,还有那一篮子新鲜的青草,让小巷的空气也变得甜润起来。 那时,还不满十七岁的我高中毕业,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有大把的时间,调朱弄粉在纸上勾勾画画之余,闲坐在门口的回廊上,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我知道,邻居那个爱采彼岸花的小婷,爱上了她的远房表亲,一位骑凤凰牌自行车的小伙子。每当她回家的时候,如果看见自家门口停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她顿时轻盈欢快得如燕子,快步如飞地跑回家。只是最常见的是家门口空空如也,铺满一地的鹅卵石泛着幽幽的光,几只蜻蜓在半空中滑翔、停驻。小婷垂头丧气,一天的劳累变成灌在双脚上的铅块,眼看着她步履沉重、心情抑郁的身影,我觉得巷子里的阳光灰暗了下来,不那么澄澈明亮了。 老了时光,旧了衣衫。那个爱穿蓝裤子白衬衫的少年,已经年过五旬,形同沧桑老树,有了风骨。他眼里的彼岸花只有旧的颜色。 作者风采 李晓斌,年11月出生,江西莲花人,系江西省作协会员、莲花县作协副主席、莲花县政协委员。供职于某行政机关。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散文选刊》《散文百家》《创作评谭》《民间文学》《中华辞赋》《诗词月刊》等刊物,著有《远岸遥灯》《故垒西边》《新诗讲义》等,与人合著《初心——甘祖昌传》。 “金鳌洲”投稿邮箱:jaz.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isuana.com/ssgy/5444.html
- 上一篇文章: 君子兰淡如水的陪伴
- 下一篇文章: 生活中的潜在危机这7个习惯趁早改第一个